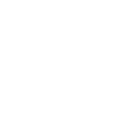作者:陳俊欽
這是一段真實發生過的事情,也是筆者很少數能夠透露的故事──其他絕大多數的心理治療都受到嚴格的保密原則所侷限,而守密是在心理治療界存活的必要條件之一。而這個「治療實例」最有趣的地方也就在這裡:整個對話完全在公開場合發生,在場至少還有其他十幾個人,當事人不但不知道也不認為筆者正在改寫他的生命故事,即便筆者反覆解釋與告知,包括當事人在那的十幾個人,都堅持那只是一場閒聊,所以還要求筆者「不要那麼嚴肅啦!但說無妨。」。那十幾個人對當事人並不熟,在整個對話的過程中,還常常七嘴八舌地介入談話當中。而令人最著迷的,就是在天不時(只有短短十幾分鐘)、地不利(公開場合)、人不和(一堆人七嘴八舌)的狀態下,治療效果就傳達出去,讓當事人戲劇性地改變了。
那是一位歐吉桑,在公開場合談起他「悲慘的一生」,順便發出一些「我歹命喔!」的感嘆。筆者忍不住就在不收費的前提下跟他聊起來。歐吉桑說到:「他小時的時候就很苦,長大以後也很苦,成年之後還是苦,到了現在孓然一身更是苦。」
故事的大綱倒是很平常:年輕的時候,他家境不好;沒有什麼受教育的機會;長大以後只能找到很低階的工作;靠著微薄的收入養家活口;如今小孩長大了,他進入空巢期,更是倍感寂寞。他回首一生,實在找不到人活著是要幹什麼的。
「那你還記得:你小時後的生活大概是什麼樣子嗎?」筆者問。
歐吉桑扯了一堆,然後又開始怨嘆人生苦悶。
「有沒有比較具體的。譬如一個畫面,一個情景等等的。」筆者問。
「有!」歐吉桑想了想。「我記得有一天,我被趕出來,蹲在路邊,旁邊是我最寶貝的狗,牠死了。」
根據這個學派,「同理」雖然重要,但是比不上「尋找生命閃亮點」與「尋找生命貴人」這兩件事情的重要(關於這兩點,筆者在拙作「搶救自殺行動」(遠流)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明)。所以,筆者在當下,決定不同理,而繼續追問細節:
「你的狗狗叫什麼名字?」
歐吉桑愣住了。想了很久,才擠出一個名字。「奇怪了,我怎麼不太記得她的名字了?應該叫做小黑吧?」
「他叫做小黑,所以是他的毛是黑色的囉?」
「好像也不是這樣,牠是路邊撿到的土狗,什麼顏色都有,土黃的啦!白的啦!東一塊,西一塊的。你問到我這個,我倒要想一想。」
歐吉桑只有思索片刻,就又說了一些。「應該是這樣吧?」
「他是短毛還是長毛的?」
「不長也不短。」歐吉桑的反應到很快。剎那間,我知道這段「治療」上軌道了。「你會摸他嗎?摸起來感覺怎樣?」
歐吉桑點點頭,但是問到觸感,又是扯了一堆。「我是說,摸起來,手上的感覺是如何?那時候,你還是小孩,手應該比較柔軟吧!」我問。
歐吉桑露出迷惑的神情。「大概還記得。軟軟的,很溫暖,很舒服。」
在後續的對話中,我不斷追問著這隻狗的模樣、大小、脾氣,甚至牠濕潤的鼻子碰觸在當年還是小孩的歐吉桑身上的感覺。我同樣也問到:他怎麼跟這隻狗玩的。
歐吉桑的話漸漸多起來了,我知道他已經回憶到更多跟小黑的事情,旁邊的歐巴桑、歐吉桑也好奇地轉過來聽,偶爾還會發發自己的意見,例如:「好可愛喔!」之類的話語。歐吉桑越講越起勁,在我的引導下,也開始提到他跟小黑去過的地方,包括魚市場啦、附近公園啦、小學操場啦等等的。遇到歐吉桑說不下去的地方,例如:小黑不能進他家等等的,我就問他家大門的顏色;如果提到學校,我就問他升旗地時候,喇叭都會放什麼進行曲,請他哼哼看;放學時,路隊又要怎麼排?如果他提到父親很喜歡喝醉酒就揍他,我就問他是否有成功躲開,甚至回頭捉弄他父親的故事。結果還真的有!歐吉桑講了一卡車的這類故事。
當然,基於職業道德,我嚴格避免問及任何深層的情感或者是隱私的故事,也儘可能讓所有素材保持在「俗世聊天」下允許討論的,畢竟,當事人真的認為我是在跟他聊天。任何過度深入的詢問,都是一種失禮的表現,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──我必須能夠控制住所有可能的負面情緒潰決。
在我所隱藏的戒慎恐懼中,我看到他的表情變了,臉上的沮喪與無助一掃而空,取而代之的,是混雜了得意、興奮、滿足、快樂的模樣,他甚至說了附近某某賣菜的阿姨,都會包庇他,讓他躲到她家去逃難的經驗,還又另外一個叫王伯之類的,也很疼他的小黑之類的。
突然之間,歐吉桑停了下來,側著頭,想了想。「奇怪!被你一說,還真的哩!我的過去好像過的還很快樂的。怎麼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樣?當時雖然生活苦,但是很有趣,而且好多人關心我。不只那些好心人,我的同學,也常常幫我的忙。」
歐吉桑當然不知道,我正在交叉使用「生命彩繪」、「生命閃亮點」與「生命貴人」等等多重技術,重新改寫他的生命。他就像我筆下的小說人物,原本是很平板的故事,但是經過各種小說手法,他的過去越來越充實,越來越有豐富,也越來越有「可讀性」──當然,在治療中,這不叫作可讀性,而叫做「有趣」、「好好玩」、「有意思」。附近的中老年人也都一一加入對話,我猜,他們大概把我當成是一個好奇的年輕人吧?
基於系統治療理論,我最後還是得進行紮根動作,所以我問了:「那你多久沒回到你說的那個地方了?」
「好久囉!」歐吉桑愣了一下,又恢復興奮:「對!被你這樣一說,我倒要趕快去看看,我沒想到,我當時還跑過那麼多地方。那根絆倒我老爸、讓他一路滾下來的那個水泥坑洞,不知道還在不在那裡?」
「你剛才說的那幾個小學的好朋友呢?」
「好久沒聯絡囉!」歐吉桑說。「他們也都老了啦!」
「那你還不去看看?」
「我等一下就會去看。對喔!再不看說不定死光了,怎麼辦?」
附近歐巴桑就開始吐他槽。「我認識有人在牽亡的,要不要介紹你認識?」
我開始感覺到:整個氣氛都熱絡起來了。顯然的,他們一同來到那個地方已經很久了(我忘了是在等車還是什麼?),彼此都見過,但是彼此都無法深談。如今,過去的紮根(回到老地方、與老友見面)跟現在的紮根(認識新朋友)都已經完成。我的「治療」已經結束了。我表露了身分,也說明了我的動作。結果十幾個年齡相仿的人,問的話都大同小異:「喔!沒付錢不好意思啦!我這邊有一百塊,當做醫藥費啦!要不要刷健保卡?」
「喔!一百塊也敢拿出來。人家醫生哪!要有誠意啊!好歹也拿一千。」一個歐巴桑說。
「那有這麼貴的。」另外那歐吉桑抗議了。歐巴桑也笑了。「說笑的,你也當真!」
「就像你們說的,聊聊天而已,何必那麼當真?」我表明這是不收費的。因為本來就不是很正式的治療。何況,我根本不打算透露我真正收費的標準。沒事何必嚇這些辛苦的藍領階級?
後來,他們變成了一群朋友,因為我知道他們會相約去爬山。我反倒很少有機會經過那邊了。改變已經造成。沒人認同那是一場「治療」,外觀上,也根本不像治療,但效果已經發生,雖然,只有筆者知道自己在二十幾分鐘內,一共交叉使用了多少技術,但是,又何必讓他們知道?何必談到「生命改寫技術」?何必談到「外化技巧」?何必談到「充權理論」?何必談到learned helplessness, sparkle life theory、reframing skill、narrative rewriting skill?何必談到「痛苦的記憶往往被認知所擴大」?何必談到「系統理論」?何必談到學習心理學中的場地論?何必談到「當事人內射了他父親的價值,而其母親採取被動攻擊的姿態,利用受害者身分,誘發身為長子的他,來對抗他父親?讓他內射的父親價值與對母親的同情產生重大矛盾。而他為了對抗自己的無助感,而承受過高風險的投資,失利後產生憂鬱,又因為自己否定自己是好的而過度嚴苛要求小孩,讓小孩急於離開家庭,也讓夫妻感情不和」?何必談到「海德格說的存有性焦慮與良心的呼喚」?何必談到「多認識朋友,多運動」?何必在「使不使用抗憂鬱劑之間掙扎」?何必在建立他的病識感上多所著墨?
主條目:精神相關 【治療相關】 關係專區 心靈專區 其他相關 最新文章
【治療相關】底下的細目:【關於治療】 人格議題 肥胖問題 自殺問題 安眠藥專論 物質濫用